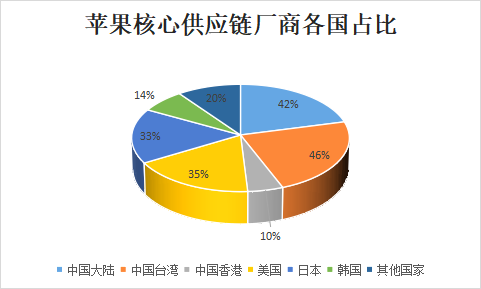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通胀削减法案”,以史无前例的3700亿美元投入来扶持国内的绿色产业和能源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的纲领把上述举措提到能源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支持能源转型和清洁生产是为了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保证美国的就业和产品都能以绿色和低碳的形式、同中国形成泾渭分明的“净”“脏”之别。
将气候变化视为国家安全议题的研究在气候学术界起步较早,但早期的气候变化安全研究仅仅将气候变化对国防、工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逐渐将气候行动同国家安全进行深度捆绑。这一时期美国学界和政界所表达的气候安全观将大国对抗逻辑裹挟到气候行动目标中,同传统气候安全观把气候变化视为人类共同威胁的基调迥然不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西方国家如何使用气候行动议题维护其国家安全、特别是霸权地位的手法进行剖析,以在维护全球气候行动大局的情况下精准拆解其针对中国发展可能采取的打压举措。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相推出美国版碳关税机制,共同点之一就是将削弱中国制造业、排斥中国高碳排放商品视为维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民主党议员怀特豪斯等发起“清洁竞争法案”,要求从2024年起,就美国国内生产和进口的化石燃料、精炼石油产品等14类工业产品,对生产过程中超出其规定碳排放水平的部分征收55美元/吨的碳关税。美国,尤其是民主党州在上述产业中具有较低的碳排放密度,因此民主党议员认为通过施加这类碳关税将有助于提高美国清洁制造业的竞争力,并打击共和党。共和党传统上被认为消极对待气候行动,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6月宣布了一项“能源、气候和保护”行动计划。在该计划的“美国创新”和“击败中俄”两个门类中,共和党只针对钢铁等国际贸易商品征收碳关税,其无视WTO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加明显。
在经济和产业政策之外,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还将气候问题同人权问题进行捆绑。它们试图通过引入全球气候安全机制,颠覆既定的气候责任认定机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气候治理责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逐渐将“国家主权安全”视为一种过时学说,而把超越国家边界的“人类安全观”视为能够应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新型安全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里归纳了7类威胁人类安全的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环境安全威胁。这种归纳方法使得“人类安全观”的理念可以直接覆盖气候变化威胁。但是,人类安全观的产生和演变具有强烈的西方人权观色彩,它淡化国家主权的倾向很可能给美西方以人权问题为由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所谓理论依据。
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关于一项决议的争辩,似乎暗示着这种将人权、安全和气候变化糅合在一起的西方话语正在对国际治理格局产生影响。安理会去年12月13日以12票支持、2票反对(俄罗斯与印度)和1票弃权(中国)的结果否决了尼日尔和爱尔兰提出的将气候变化关联的安全议题整合进预防冲突工作的机制中。中方在解释自己立场时强调,各方应该防范气候议题的泛安全化。在国际气候行动议程中,中方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别的原则,这一原则清晰地界定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承担维和行动等预防冲突工作中具有比较高的责任权重。如果将气候安全议题整合进预防冲突工作机制,实际上是试图以安理会成员国责任为基础去设置各国在气候行动中的应尽义务。这将在本质上弱化甚至令西方发达国家逃避它们的历史责任,也很可能推高中国的责任。这对我们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原则。
应对气候变化同发展人权一样,始终是负责任国家致力于追寻的目标。但过去几十年西方某些国家对人权议题的政治化操弄,将“发展人权”堕化为谋求霸权的工具。如今,一个不好的迹象是,气候行动似乎也在沿着类似轨迹发展。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国际气候行动中的合作面与斗争面共存的复杂关系,尤其要找寻有力的气候治理话语体系,瓦解西方在这一议题上的所谓“道德制高点”,并同国内外真正关切气候变化的人一道抵制西方某些国家对气候议题的欺骗性政治操弄。